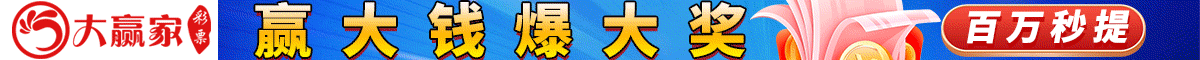榆树湾的故事01-13
(一)
榆树湾没有榆树,一棵也没有!
这是个小村子,村子外面有一条河,河不大,但也不小,有二十多米宽,村里人把它称着“江”,本来河边曾经有过一排排的榆树,但在大跃进的时候全部砍来炼钢铁了,现在还留下几个树桩立在河滩里。
河水挺深,悠长连绵,村子上游几里的地方才有一座桥,因为是邻村自己集资修建的,所以村里人有骨气,都不去走那个桥,都愿意每次掏个几角钱坐老杜的渡船过河。
渡口就在村子外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刚长大的榆树,这是榆树湾最后的一棵榆树了,老杜的船就系在树上,没事的时候,老杜喜欢坐在树下拉拉胡琴,琴声不能引来村里人,但是常常引来几只狗趴在地上听。
老杜今年五十岁,年青时也是个风流人物,走东窜西,见了不少市面,在村民威望颇高,只可惜怀才不遇,到头来落了个清静,天天在这渡船上悠闲自得,无人过渡时这船便成了渔船,都市人来了,便见老杜头戴斗笠,独钓船头,无比安详,往往疑为隐叟,称其高人。
老杜有家,但他一般不爱回去,睡也睡在船上。晚上的时候,他喜欢坐在船头,对着静静的河水拉他的胡琴,或者点着油灯看一本唐诗宋词,颇有些古意。
看一回书后,老杜会出一会神,抽一袋烟,看着不远处那寂静漆黑的村庄,若有所思,村子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散于荒野之中。然后,老杜会倒头大睡,直到天亮。
天还没有亮,渡口已经有人在叫老杜的名字了,老杜起来一看,李新民和他儿子李小柱站在渡口,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老杜就问:“是新民呀,这么早要上哪儿去?”
“回学校去呢,今天开学,就走早一点,没吵着你睡觉吧!”李新民边说边就上了船。
李小柱帮他把东西全扛上船,又跳下船来说:“爹,我先回去了!你路上小心点!”
李新民点点头,说:“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多帮你娘做点活,不要偷懒。”
李小柱点点,朝村子里走去。
李新民是镇上中学的老师,也是榆树湾里唯一的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今年四十五六,前不久才提了副校长,很是春风得意。李小柱是他儿子,今年刚高中毕业,成绩太差,没考上大学,也就没心念书了,呆在家里干活。
老杜就撑起船向对面划去,边和李新民说话,盛夏的清晨有些清冷,原野里弥漫着雾气,看着李新民的身影消失在雾气里,老杜撑着船回去,天还没有亮,村子里传来鸡叫声,老杜打了个哈欠,又想睡觉了。
李小柱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村子里,两只狗尽职的叫了起来,他骂了一声,向家走去,院子里有一棵枣树,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李小柱看见自己屋里的灯还亮着,想起刚才出门时忘了关了,就过去把灯拉熄,然后向东厢房走去,路过妹妹小红的房前才想起妹妹这几天到二姨家去了,很高兴,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东厢房是李新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李新民刚走,里面静悄悄的,李小柱推了推门,轻轻地叫了一声:“娘,我回来了。”
然后回头看了一下周围,天边有些发白,村子里很安静。这时里面灯亮了,脚步声响起,然后门轻轻地打开了。
李小柱钻进屋去,转身关上门,刘玉梅看了儿子一眼,又走到床前,躺了下来,问:“你爹走了?”
李小柱点了点头,说:“走了,过河了。”
刘玉梅白了他一眼,说:“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你爹刚走,你就不怕他又回来?”
“不怕,他要赶车呢!”李小柱说着,也到床上躺着,说,“爹带的东西真多,把我的肩都扛疼了。”
刘玉梅咯咯地笑了,说:“这都是报应,活该,你就盼着你爹早点走吧?小子,又痒了?”
李小柱点点头,说:“早就痒了,爹回家这两个月都没什么机会,可憋死我了。”
“死相,才这点时间你就忍不住了?那你去把灯关上,我还要睡觉呢,你自己弄,可别吵着我了。”刘玉梅忍不住戮了儿子一下,笑着说,“你们俩父子都是牛,几天不喂就受不了,去吧,关灯。”
李小柱并不去关灯,说:“怕啥呢?小妹又不在家,家里没人了,怕个啥呢?”
刘玉梅不讲话了,转过身子闭上眼睛,说:“你可轻点,我还要睡觉呢,你爹也弄了半夜,刚擦干净身子你又来了。”
刘玉梅虽说已四十出头了,可常年劳作,身体保持得不错,健康饱满,像个熟透了的桃子,穿着短褂短裤躺在床上,散发出一股诱人的气息。
李小柱就来劲了,伸手就在她的大腿上摸,摸得刘玉梅发痒,闭着眼睛咯咯地笑,然后伸手在儿子屁股上捏了一把,说:“你不快一点,天可要亮了!”
李小柱就加快了动作,掀起母亲的短褂,露出雪白的上身,那对奶子倒还饱满,像两只大馒头一样,李小柱兴奋地又摸又揉,很快,那两个紫红的乳头就立了起来,刘玉梅也轻轻地哼了哼,显得很满意。
好容易玩完了母亲的乳房,李小柱又把手伸到她那对肥大雪白的屁股上,常年的劳作使得刘玉梅的臀部显得浑圆紧绷,结实得像个小姑娘的屁股,摸上去很光滑,李小柱搞得爱不释手,伸手要脱内裤,没有脱得下来,哼了一声,说:“娘,怎么不让脱呀?”
刘玉梅忍住笑,抬了抬屁股,让儿子把短裤脱下来,说:“有什么好摸的,你以为那是脸蛋呀?”
李小柱笑笑,说:“娘的屁股比别的女人的脸蛋还要漂亮呢!”
刘玉梅咯咯笑得喘不过气来,说:“那你就把它当成脸蛋吧,那你还不亲这个脸蛋几口?”
李小柱就低下头去亲,刘玉梅忙翘起屁股让儿子亲。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