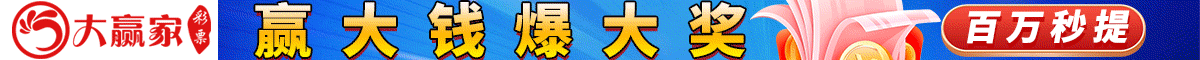为人师表下的乱伦
《为人师表下的乱伦》上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可以称高寿,我还算健康,生活能自理,没有老年痴呆。有时候,我宁可自己老年痴呆,宁可自己早些死去,不想天天期盼上大学的小孙女在电话里急匆匆一句「奶奶,我好着呢,您长命百岁。拜!」也不要在孤独时的时光里,回忆那些酸涩往事,还有那些想爱不能爱,想见无法见的亲人们。
可是,七十八岁的我除了坐在门前晒太阳,我还能做什么?多年来,我一直对别人说我是孤儿,除了我那早亡的丈夫,我身边所有亲人都不曾知道,我不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我有父母,有弟妹,我的孩子也是有舅舅有姨妈的。当然,过去的我不会知道,亲人之间的怨恨,在临近死亡的岁月里会变成无尽的思念,还有些许的悔恨。
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我家门前有山,有水,缺吃的,在山坡上采野菜,拾「地皮」,没烧的,去山林里捡枯树枝,摘松果。那些年,所有的艰苦都是我自找的。在困苦里,能让我疲惫的心忘掉伤痛,回归安宁,只有他,我那死去太早的丈夫,一个小我六岁的山野汉子恩赐予我的。
如今我的父母想必是已故去,他们应该早将我遗忘,我也曾忘却,只是如今突然想知道他们的晚年是如何度过的,是否也曾如我一般儿孙绕膝?当然他们失去了一个女儿,他们是否也有过如我牵挂着远在省城读书的小孙女一般牵挂过我呢?
我后面还有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如今还好吗?我从没告诉过孩子们,他们还有两个舅舅一个姨妈。一个人可以没有朋友,但是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没有亲人。孩子们过去总爱说我妈妈是孤儿,所以我们没有舅舅姨妈这样的亲戚,可他们不知道我让他们缺失外公外婆,舅舅姨妈,是因为我要遗忘我的父母,还要遗忘一个大我不到两岁,和我一起长大,犹如青梅竹马的小舅舅。
我母亲是解放前江南一地主家里的大女儿,去城里读了几天书,跑出去闹革命,三年不见家人,再回家送给我外婆的礼物就是不到半岁的我。那时候我外婆正抱着她自己最小的儿子,小弟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大姐姐,可能他更喜欢大姐姐的女儿吧,听外婆常说那天小舅舅握着摇篮里我的小手,我和小舅舅相互对视着咯咯地笑。
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咯咯地笑声有罪吗?有罪,它是罪恶的温床,是我小舅舅孤独凄凉一生的导火索。也是我背井离乡,抛弃亲人,幽居山野的最初根源。
我为什么会给这个故事标题写「为人师表下的乱伦」?这是一个人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伪君子,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义正言辞训斥我的一句话,他的这一句话让我的小舅舅经历十年牢狱,最后精神颓废一蹶不振。
当年,母亲和父亲闹革命去了,留下我跟着外婆在苏州乡下无忧无虑的度日。我喊外婆,我的小舅舅喊母亲,我和小舅手牵手一起长大,一起上学,朦胧中我仿佛忘了我是谁,小舅可能也忘了我是他大姐的女儿,我们就像是林黛玉遇到了贾宝玉,那个抚养我们长大的我的外婆,小舅的母亲,就像是《红楼梦》里的贾母。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丰衣足食,狭小且宁静的小村庄,幸福快乐的日子,一直到我和舅舅一起读高小。突然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外婆喜上眉梢,忙里忙外。我和我的小舅舅却茫然无措,我不知道如何喊一个陌生女人「妈妈」,小舅舅一句「大姐」喊的胆胆怯怯。
我十五岁上高中的那年,不到十七岁的小舅对我说,高中远离家乡,我们不要在对别人讲我们两人的关系,我们努力考大学,最好到南方去,找个远远的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们一起生活,永远在一起。
那些年父亲和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在沈阳,他们要带我过去,我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外婆也说舍不得我离开,我留在外婆身边和小舅舅一起读书,生活。小学初中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高中远离家乡,也很幸运被分到同一个班了,小舅舅成绩很出色,老师们都希望他考去北京,或者去上海,最后他只填报了湖北的一所师范高校,分数出来了所有人都为他可惜,只有他和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是依我的成绩为准,只填报了唯一一个志愿,之所以填师范大学,也是因为那些年师范生由国家承担食宿,这样我们可以少问家人要生活费,亦可以少写信联络。
年轻的我们在感情的世界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陷在错误里难以自拔,我们只想远离熟悉我们的亲人朋友,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忘掉我们两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就当我们是初相识,没有过去的点点滴滴,只盼有未来的天荒地老。
我和小舅舅如愿以偿的考上了湖北那所师范高校,小舅舅录取的是数学系,我进入了历史系。因为和父母相距甚远,从小离别的隔阂,母亲就像当年把我交给外婆一样,上大学后,又放心地把我拜托给自己的小弟弟,在大学里多多照顾。
大学里,我和小舅舅开始以老乡老同学的分身出双入对,有校领导,系指导员警告我们,大学生不许谈恋爱,我们也接受批评说没有谈恋爱,只是老乡,老同学,太熟悉了,所以经常一起。
大二那年,高我们两届的同系学长留校做了校团委书记,他开始有意无意的接近我,还暗示我,如果我同意,他以后可以帮我留校。我说国家到处缺人才,不是号召我们都下乡嘛,偏远地区最需要我们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呀。他冷笑两声说,你吃得了那个苦吗?我很坚定的告诉他,我可以吃苦。他说我都是为你好呀!
我当时不知道,他的那句为我好,后来差点把我逼上绝路,那时我满脑子都是我的小舅舅,小舅舅早和我做好打算了,我们毕业后远离城市,到最偏远的地方,交通不便的山区学校,那里没人知道我和小舅舅的血缘关系,我们作为大学同学一同去教书,遗忘父母,遗忘亲人,就我们两个,像孤儿院出来的一对患难情侣,我们结婚,一辈子在一起。
未完待续,虚构小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017年11月4日
《为人师表下的乱伦》中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最能表达年轻时的爱情,可是我的爱情,那是爱情吗?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词「乱伦」,早已在我们感情萌芽之时,就已经将我们那份感情的灵魂扣在了地狱里。无论我们后来怎么挣扎,都逃不脱被世人耻笑,被亲人责骂,被自己残存的理性思维与不能自已的情感纠结而苦恼着。
从小到大,小舅舅都陪在我身边,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知音,我的世界里只有他。小时候,我们上学放学都在一起,白天黑夜也都在一起,过去农村读书的女孩子不多,即使有,也没有跟我特别要好的,因为我有什么事都去跟我的小舅舅说,我不需要闺蜜,我的小舅也是我的闺蜜。
上大学后,我和小舅不在一个系,又被学校警告说大学生不许谈恋爱,不然通报批评,严重者通知家长,甚至开除学籍都有可能。这样我和小舅被人为的,也是自动的保持着距离,然后我渐渐开始有联系密切的女同学了。女生之间发展成闺蜜是很容易的事,两个女生一起上街买同一款式的裙子,那么我们就是好朋友了,一起去照相馆照一张登记照,然后被照相师傅游说着再照一张合影吧,这样两个女生又成了无话不说的知音。
现在回想,我和莲的友谊应该是从那个校团支书的学长经常来找我开始的,学长找我说,听说我是苏州女孩,想必会唱歌跳舞的,希望我参加校学生会,做一个文娱宣传的骨干,带动着全校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丰富起来。在学长的推荐下,我成了学生会里的文娱委员。周末学校大会堂里,我几乎成为舞会上的交谊舞皇后,我的舞伴是我小舅舅,一个甜美温柔,一个风流倜傥,在那个人们生活水平还很艰苦的年代,我和小舅双双舞出的优美舞姿,无疑成为校园的焦点。我们每曲必跳,校团支部书记没有机会约到我,曾愤愤不平地对我小舅舅说:「听说你是地主家的公子,难怪小资情调浓厚,不过一个数学系的,能跟我们学文史的人一样富有精神内涵吗?」
小舅舅是地主家的孩子,从小知道如今的社会,他这样身份的人不能跟那些贫苦劳动人民出身的人争论什么心灵美好。所以小舅听了那些话也不辩解,事后让我以后少跟那个团支书学长交往,我也点头同意。然后我以学业为重,辞去了校学生会的工作。
学长找我几次,劝我留在学生会,说以后毕业留校,做学生会工作的也是有利条件。我说我没想过留校。后来,莲问我为什么不做学生会的工作了?我说我不想做了。莲说,你看团支书总来找你,你还不去,要是我还求之不得呢。我说好,以后我跟团支书说让你去。莲开心地说,好啊,好啊。
再遇到团支书来找我劝说我继续留在学生会,我就向他推荐了莲,团支书说,你呀,有点不知好歹,我这可都是在帮你,你实在不去,我就让莲去了,好多人求着我,我都没理的,特意空着文娱委员的位置给你,你不去,我还是满足你推荐的人,让莲去,这也还是为了帮你。
莲成为了校学生会的干部,有一段时间很忙碌,不再跟我周末相约去省城江边溜达,我跟小舅舅也不敢见面太多,主要是怕学校通知家长。有一回,莲邀我去校园树林边的长椅上坐坐聊聊天,我问她,你周末学生会没事?她说没事,好久没跟你谈谈心了,想跟你说说话,我把你当知心朋友呢,你把我当朋友吗?
我说我当然把你当朋友啊。莲说,可你不对我说心里话。我说我有什么都跟你说的呀。莲说我问你,你跟数学系的你那个老乡到底什么关系?我傻呆呆的问莲,你知道我跟他的关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莲嘿嘿一笑说,瞧你那紧张样,看到你们三天两头的,不是你找他就是他找你,我又不傻,猜也猜到了。我长长舒了一口气说,哦,你说的是我们两个谈恋爱呀。莲观察到我前后神态的变化,疑惑的问,难道除了恋爱还有别的?我说没有,就是恋爱。莲说我不信,你一定还有什么瞒着我。我说没有,莲伸出手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你还有心事瞒着我,你完全没把我当贴心人啊。我说真的,没有什么瞒着你的。莲说我很伤心,你没把我当朋友。我犹豫一会儿说,我说了,你不能告诉别人。莲说我保证替你保密。
如果说人世间,亲人之间突然反目为仇是最为悲哀的事,那么能在这样悲哀中雪上加霜的一件事,是你发现自己认为最可信的闺蜜轻描淡写之间就背叛了你。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经历了这所有一切人世间最痛苦的情感纠葛。我的闺蜜背叛了我,我的父亲恨不得对我的小舅舅举刀相向,最后父亲在怒吼中,听信那个伪君子校团支书的话,完全无视我的所有解释,终将无辜的小舅送入大牢。
那是临近毕业时,大学里成双成对的多起来,还有的直接找学校要求能照顾分到同一地方,学校也开始默许学生之间的恋爱。小舅找我商量着,怎么找学校表达我们两人希望能分到一个地方,并且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志愿容易申请,只是不能过分宣扬,尽量不能让家里人早早知道我们的去向,我们梦想着某天跟家人完全失去联络,即使后来他们在找到我们,那时面对生米煮成熟饭的我们,家人都会忍让一步,跟我们断绝关系,留我们自生自灭,让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梦幻天堂里。
我们的申请还没有提交,团支书先找到我了,他首先劝我留校?跟他在一起。我说我有心上人,我们都愿意去祖国最偏远地区。他说你别做梦了,学校早就知道数学系你的那个老乡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你不要傻乎乎地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我惊讶着问他,是谁告诉你的?他说这你不用管,你只要答应和我在一起,我一定想办法让你留校。我说我不留校,我到哪里都可以,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我要离开,团支书拦住我,他说我今天要好好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必须听我的,只有我才能为你的将来做最好的准备。我说我不需要,再说我也不喜欢你。团支书再一次拦住我,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了,甚至抱住了我。我对他怒吼到,你放开,不然我喊人了。团支书说今天休息,这里没人,再说你和你舅舅的事,你想传出去很精彩吧。我有些胆怯了,不敢喊叫,只能努力地拼命地想摆脱他的纠缠。
我无法挣脱团支书对我实施畜生般的暴力,就在我几乎绝望时,我听到小舅舅喊我的名字,我立马鼓起勇气哭喊着,要小舅快来救我。团支书这时也在惊慌失措中住手。我迅速跑去打开办公室的门,见到小舅的一瞬,我的眼泪随着我一声「哇」的呼叫奔涌而出。小舅随即跑来,即刻便明白发生了什么,然后小舅和团支书扭打在一起。
愤怒的小舅拼命地,不顾死活的和团支书对打,我呆呆地站在一边,团支书这时惊恐万分的大声呼喊起来。很快就有人发现了,最后校领导将我们三个带走,驱散了围观的同学。我满腹委屈的跟校领导诉说,团支书如何诱惑我,还想强奸我,然后我的小舅,当时我对外说的是我的老乡如何发现了来救我,我的老乡是为了保护我才跟那个畜生团支书打架的。
团支书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我和小舅的命运,他听到我骂他畜生时,回答说,你们两个才是畜生呢,我关心你们,劝导你们,你们不知道好歹,还打伤我。团支书对一脸茫然的对校领导说,他们两个是亲舅舅和亲外甥女的关系,却不顾伦理,还想脱离家庭,两人恋爱结婚。学校能允许吗?这个社会能允许吗?难道让我们的学生看着自己的人民教师在为人师表之下乱伦吗?
小舅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怯怯地重复着一句「没有,没有。」团支书接着说,这是莲告诉我的,是你亲口对莲说的,你们要远走高飞,找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两个人恩爱白头。
这之后我除了眼泪,再无能力为自己辩解,小舅舅也一直沉默着,面对询问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时,他用点头的方式承认了我们的血缘,还有恋爱关系。学校迅速打长途电话找到了我的父母,父亲来到学校得知我跟小舅舅之间的事情后勃然大怒,在校团支书的怂恿下,父亲选择报警,乱伦是一大罪过,团支书欲强奸我时,被我用手抓伤的脸也成了他作为受害人受伤的证据,这些都让小舅舅一人承担了,甚至都没有法庭受审宣判,小舅被警察拷走,然后以乱伦强奸罪劳改十年。
未完待续,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017年11月5日
《为人师表下的乱伦》 下

眼泪只能加重悲伤,减轻悲伤的唯一法宝是时间,小舅被抓后的一段日子,我是在眼泪的浸泡里度过的。那些哭泣的日子里,我什至有想过一死了之,最后我仿佛是哭干了眼泪,麻木的吃饭睡觉,唯一清醒的就是跟学校提出分配到偏远山区的要求,只要是能离父母远的地方都行。我还抱着希望,等小舅刑满释放能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不要再跟父母往来,父亲已经被我气疯了,怒吼着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我用沉默表达着怨恨和执拗,也用沉默对抗所有指责我的亲人。
我曾问过莲,为什么不守信用?说好不对任何人说关于我和小舅舅之间的事,怎么还是告诉了团支书?莲说,你跟你小舅舅有秘密吗?团支书和我的关系就像你和你小舅一样,有什么值得隐瞒的。我泪眼朦胧的呆望着莲,听她继续说道:「不对,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他说让我毕业后留校,然后我们会结婚,我们会很幸福,很幸福的。你们是乱伦,不会有结果,只会被诅咒。」
后来我从学校直接去了分配单位,我不想回父母家,外婆家也不能去,听说外婆为此事气病后离开乡下去城里大舅家里了。去报导的途中,我发了一封信,我不知道小舅关押的详细地址,按我所知道的写了一个,信的内容也很简单,几句问候和关心,落款用了「历史」的英文单词,最后在信里留下了我即将去往的学校名称。小舅是认识我的字的,如果他能收到信,他一定会明白我的心意。
我要去工作的那个学校不在县城里,离县城有二十里的路程,不通车,都是山区小路。我到了县城,先去县里的教委办公室报导,那里已经有学校派去的人在等候我,等我的人不说话,只是自己拿根扁担帮我挑起行李,带领我去往学校。我问他:你也是新分来的吗?你教什么课?那人有些羞涩,回答说他不是老师,他只是学校食堂里打杂的工人。我说看你这么年轻,以为你也是刚刚学校毕业的呢。我又问他:「师傅您贵姓?」他说他姓刘,叫他小刘就好。
路上,小刘挑着一头是棉被一头是行李箱的扁担,在不算太热的天里,汗流浃背。我有些不忍,想要自己挑一会儿路程,小刘不让,我便找些话题来说,问他多大了,得知他才十五岁,我很奇怪他怎么这么早就出来工作?为什么不读书?他说他是顶替原来在食堂做饭的爸爸来工作的。我又问:「那你爸爸呢?」他眼光有些暗淡,说生病死了。话题说到了伤心处,我不知道如何安慰眼前这个小男孩,却突然连想起自己的父亲了,隐约中寻思着如果我的爸爸死了,我到底是该高兴还是伤心呢?我有些茫然,然后加快脚步,让自己努力接近即将到来的陌生学校。我要投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遗忘过去,除了小舅,其他的最好都彼此忘掉。
我去了这个偏远小县城的一所初级中学,听人说,我报导前,学校就炸开了锅,第一次有名牌大学毕业生分到那里,传说是个美女。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随后人们也都知道美女在学校档案里有记大过处分,至于是什么原因而受处分,人们只能凭想像力,猜测出个五花八门来。每年学校都会派人去县城里接新分配来的老师,大多是派年轻男老师接新同事,一来男老师有力气可以帮着拿行李,二来同样是老师,大家有共同语言一路上聊天不寂寞。轮到派人接我的时候,学校领导有些为难,因为一个在学校有记过处分的女生,有的老师不愿意来接,有愿意来的,领导又不让,校领导以安全起见,按排了上班不久在食堂里打杂的小刘,理由是顺道让小孩子去县城见见世面。
那几年出身不好的人总是被嫌弃的,尤其名声又遭贬损的女人会更加被人瞧不起。我总归还是占了父母早年跟随共产党的光,成为了一个革命者的后代,才平安无事的继续享受着国家那些年对大学毕业生负责到底的政策,安排工作,享受着有工资有粮贴的城市户口待遇。而我的小舅舅作为地主家的后代,得罪了作革命工作的姐夫,联合着其他革命人,被打入万劫不复。
我不知道人活世上有没有一种命运掌控,或者是祸福有因。现在想想,我父亲让我外婆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同样也失去了一个女儿。当年学校担心我的人品有问题,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去接我,以为这样很安全,后来发生的事,也确实如此,我这一生的安全都靠着那年为我挑担的小刘了,后来,他为我扛起岁月中所有的风雨,只可惜他跟他父亲一样没有活过40岁。
一个女人独自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生活,寒暑假逢年过节都不曾离开,甚至都不跟同事提及自己的家人,这事本来就是非常态,加上后来我对所有追求我的男老师一概冷漠对待,这样更加引起人们的议论纷纷。虽然母亲也会写信来问我的状况,可我却从不回一个字,慢慢地母亲也只在过年时候来一两封信,告诉我家里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我的惦记。
学校本来就缺少女老师,少有的几个后勤女工作人员跟我也聊不到一块,偶尔有人热情待我,遇到了我的冷漠回馈,渐渐地大家也都习惯了不理我,背后无非就是说我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让有些热情的人也开始嫌弃我。
我再一次想到了「安全」这个词,当别人认为我不安全的时候,我也防备着那些防备我的人,可能人们认为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于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不会勾引他,他也没心思诱惑我。所以,每次遇到小刘,我才能舒心自然的与他微笑,亦能简单聊几句。或许正因为我那份自然亲和感,让小刘也感受到了,每次去食堂打饭,他会总会适量多给我一点好饭菜,还经常笑呵呵的给我介绍当天的饭菜种类和价格,有时候我去上课了,他会帮我打好开水送到我宿舍门口。再后来,每到放寒暑假前夕,小刘总是主动帮我劈许多柴,存放在我宿舍傍边,以防学校放假后,我自己做饭没柴烧。
一两年拒绝别人的追求不找男朋友或许还不算大问题,六七年里一直没打算出嫁那就有问题了。首先,我已经是个老姑娘了,那时候有人给二十二岁的小刘介绍对象,他没同意见面,就被人说闲话,说是有个工作就不愿意相农村对象了,人家有城市户口的姑娘也会嫌你只是食堂工人呀,再不找就成老光棍了。那个年代快三十岁还不嫁的姑娘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小刘不去相对象也成了别人嘴里议论的怪物。后来发生一件事,更加让我和小刘彻底成为人们眼中的怪物而被鄙视。
那天小刘跟平时一样帮我提来一桶热水,他知道天凉时候我爱用很多热水洗澡。我去洗澡后,听到窗外校长训斥小刘,后来才知道,校长发现小刘在我窗外徘徊,说他有意偷窥我洗澡。我对校长说算了吧,也没出什么事。校长说不能放纵这样卑鄙无耻之徒,一定要对他严厉批评教育。我央求校长放过小刘,我说我不计较就算了,我看他就像个小孩子,平时他对我也挺照顾的。
那时经常有批斗会,校长为此事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小刘,还要求大家都来批斗他,校长说希望能开一个专题批斗会,要对这样道德败坏的人狠狠的教训。校长在会上讲的口水四溅,最后因为没有人积极响应,开专题批斗会的提议不了了之。会后校长多次找我,希望我积极起来,对道德败坏的流氓不能心慈手软,校长一边说还一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回了一句说,我不觉得小刘是流氓,至少他从来没不经过我同意,随便把爪子搭我肩上。说完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学校到处都是关于我的大字报,什么道德败坏,在大学就勾引男人,到山区不积极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嫁不出,又勾引贫下中农的孩子,把一个善良的贫下中农家的孩子诱骗成了流氓。校长批评小刘,没多少人支持,但是校长因为大字报的事批评我的时候,除了小刘,没有人不支持。很快我成了大会小会批评教育的典型,以后每逢开会,别人坐着,我得站着,再后来,我不能随便站着,必须站在老师讲课的主席台上,还必须立正站好,面对台下,无论是其他老师对我的批评还是学生们的讥笑,我都得低头认罪。
接下来的日子里学校也渐渐全面停课,听说县城里有两派系的人打起来了,甚至有人抢了枪枝,准备来一场真正的战争。不久,学校里也开始出现带着红袖章的社会青年号召学生们一起打砸教室,烧毁书籍。我再一次成为抨击的主要对象,这回不再只是批斗了,还要胸前挂牌子,双手反捆着站在大操场上示众。
随即有接到通知说县里持枪的队伍打到乡下来了,可能有一场恶战要在学校展开,所有能劝说回家的学生都回家了,附近有家的老师也回去了,也有投靠亲朋好友的,反正是大家尽量不待在学校,除非自己想去参入斗争的人。我没地方可去,只能留在宿舍里。那天白天遇到小刘,我问他怎么没回家,他说家太远了,来回要走一天。我说学校不安全,他说你都没出去躲着,我怕什么?我还想说我是没地方可去,但是他已走远了,一会儿他又回头喊了一句,「你晚上关好门,注意安全。」
那天晚上确实不安全,夜里我听到木质的宿舍门栓有撬动的声响,我问了几声没人回答。安静了一会儿,突然门就开了,那时候没有电灯,晚上都是点煤油灯,半夜里我只知道有人进来了,我大喊起来,那人猛扑过来抱住我,我挣扎了一会儿,一边挣扎一边喊叫着,后来又一个人冲进来了,我知道那是小刘,因为在我和那个撬门进来的人扭打叫喊时,我听到他一边往我这边跑来,还一边在喊我的名字。小刘跑来和那人打成一团后,我才确定先前那个撬门进来的人是校长,小刘和校长打了一会儿,学校还没离校的其他员工听到动静也过来了。人们拿着煤油灯往这边走来,校长高声呼救,他让大家赶快来抓道德败坏的流氓份子。
就像上次在学校里我和我小舅舅的遭遇一样,这一次是我和小刘,当真诚的人遇到伪君子时,最能深刻体会什么叫有口难辩以及信口雌黄。小刘是红五类出生,那些勇于参加批斗的人,要小刘鼓起勇气揭发我,要小刘说出我是如何勾引他诱惑他犯罪的。无论小刘怎么辩解,人们都认定我是坏女人,认定小刘被我迷惑了,认定校长是来捉奸而被打的。
他们将我反锁在宿舍,并带走了小刘,第二天天不亮,我的门被人撬开,小刘急急忙忙让我带上换洗的衣服跟他走,他拉着我往校园侧门跑。我听到了枪声,问小刘是不是真打起来了?小刘说是的,都拿着真枪呢。
就这样我跟着小刘去了他家,家里只有小刘的妈妈,小刘还有个妹妹已经出嫁。我在小刘家里这一住就是两个月,因为学校停课了,接着又到了寒假,过年后再去学校,我们才知道,我和小刘因男女作风问题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小刘准备回乡下的家里,我问小刘,你可以带我一起走吗?小刘说只要你愿意,怎么都可以。
后来我就成了小刘的老婆,我不知道是我遗忘了我的小舅舅,还是六七年的渺无音讯让我不再抱希望了,亦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希望,我也只好换一种希望活着。跟小刘结婚三年后,当时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大女儿半岁时,女儿的大舅舅,也就是我的大弟,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我。大弟弟对我说近几年家里写给我的信都被注明「查无此人」而退回去了,所以妈妈要他来一定找到我。看见弟弟,又听说妈妈非常挂念我,我止不住地流泪,听弟弟说着外婆已经去世两年了,我一边哭一边问,「你们有小舅舅的消息吗?」弟弟犹豫了一下,告诉我小舅舅已经死了,我一下惊呆了,愣愣的看着弟弟,直到听完弟弟说小舅舅在牢里身体一直不好,出狱后又去修水利工程,不久就死了。我默默地流了一会儿泪,然后很平静的对弟弟说,你明天就走吧,以后不要来找我了,你叫妈妈不要牵挂我,就当没我这个女儿,你们也没有我这个姐姐。
后来,我跟小刘一直住在小刘老家,生活艰苦,日子却也平静安宁。许多年过去人们早已遗忘因作风问题而失去工作的两个人,我们也没有向任何人任何组织去申请。女儿十五岁,儿子十二岁那年,一向身体强壮的小刘突然有一天说他心口疼,他说当年他爸爸也是说心口疼后来死了,我们很焦急,但是山路遥远,寻医问药不方便,想着第二天翻山去那边公路上拦车,在去县城医院看病,可是当天晚上小刘就永远的离开了我和孩子们。失去小刘的我,生活更加艰苦,为了两个孩子,我跑了一趟县城教育局,请求给我一分民办教师的工作,我的申请很快如愿,我靠着这份微薄收入让我们的两个孩子走出了大山。
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