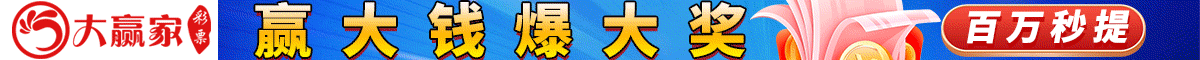《夺妻(论如何肏到别人的新娘)》 - 第六十六回:安氏
“嗯……”
沈静姝迷迷糊糊地转醒。
睁眼,只见李衿坐靠着软枕,手持一张展开的状书,就着夜明珠柔和的光默读。
淡淡的光晕勾勒出她沉冷俊美的侧颜,沈静姝被惑住,不由软软唤她:“衿儿。”
李衿视线一顿,随即偏过头。
“醒了?”
“嗯……”
沈静姝撑着榻欲坐起来,可是腿才一动,忽然感到腿根那处,传来异样的麻酸。
羞耻之地似乎有些敏感,沈静姝不禁脸红,暗道自己怎会如此……淫荡?
心中正自羞愧不已,突然被李衿强行抱过去,坐在了她的大腿上。
锦被之下的玉体不着寸缕,顷刻春光乍泄,半截莹白的身子都染上了夜明珠的柔光。
沈静姝羞不自胜,忙要去提那锦被,却又被李衿按住。
“衿儿?”
她不会又要想行那事儿吧?可是自己那处都还酸着,再由着她胡来,怕是……急要阻止李衿,她却已经掀了锦被,低头去瞧她的那处。
“方才行得猛了些,卿卿可有不舒服的?”
“……”
沈静姝粉颊彤红,暗道着不知羞,可目光也忍不住下移,望向自己的那处。
阴阜干干净净,可肉瓣却仍是艳红,小花唇竟然还微微张着,像是合不拢地吐出几丝清露。
李衿的手掌抚上无毛的白虎地,手指轻轻地拂弄两片阴唇,查看情况。
“唔……”
沈静敏感地一软,泄出闷闷的呻吟。
“想了?”
李衿笑笑,偏头在沈静姝的额上吻了吻,中指点上几滴春露,迎着穴口慢慢插进去。
“嗯……”
下腹瞬间紧绷,沈静姝蹙了蹙眉心,一夹腿根,含羞带怨地望向李衿。
“衿儿……,不要了。”
再弄下去,她那处非坏了不可!
“我不弄,就是看看给你抹的药有没有吸收。”
说着便往穴里头插,手指顺着仍旧湿滑的穴道顶进去,在深处一转。
“啊……”
沈静姝酥软地倒在李衿身上,娇喘吟吟,眼看着她把手指从那热烘烘的穴儿处进出。
“我就帮卿卿看看……”
说得冠冕堂皇,其实早已忍不住在嫩穴里捣弄。
手指一寸寸在里头抠挖,沈静姝抓住李衿的衣服,脸深深埋在她颈窝里,羞耻地咬住嘴唇。
本已经被干得麻木的穴儿,陡然又吸了手指,被摩擦得漫出热感。
李衿像是拉动琴弦弹奏,手指在穴口悠悠进出,微微勾起指尖逗弄沈静姝的敏感。
层层褶皱被指腹抚着碾平,穴道里头不住收夹,李衿又迎着深处探进,反复摩擦一个凸点。
“唔……”
沈静姝一颤,穴肉膨胀起来,却在此时,感到李衿把手指拔了出去。
一根清亮的淫丝勾出,晶莹泛着光晕。
沈静姝羞愧得快晕过去了,却见李衿悠悠将手指含进口中,吸吮。
“卿卿的水最甜了……”
清眸含笑,勾带几分戏谑,沈静姝被她暧昧的目光羞得滚烫,忙一扭身,把头埋进李衿的颈窝里去。
“不知羞!”
她小声地埋怨,可语气又分明透着欢喜。
李衿瞧她娇憨可爱,不由心旌摇曳,在沈静姝额上落下一吻。
提被遮住怀中的美人春光,李衿将沈静姝抱到身边坐着,刮了刮她的鼻尖。
“卿卿且忍一忍,待我将这些送来的折子看了,再与你行那鱼水之欢。”
鱼水之欢四字说得尤其低沉暧昧,沈静姝脸又是一红,耳根都臊起热来。
登徒子!
心里虽是如此“埋怨”,可身体去实诚地依偎着李衿,把头轻轻搁在她的肩上。
软软地靠了她一会儿,沈静姝陡然想起云六娘托付的事情,她还未曾与李衿提过!
当真是淫色误事,沈静姝暗自羞愧,急忙与李衿道:“衿儿,我有一事要与你说!”
即刻把云六娘的事情如实说了,又讲到那小哑女说的三拨人。
李衿静静地听完,末了脸色忽然有些凝重。
“怎么了?”
沈静姝见她如此,不由心惊,莫非那安氏娘子已不在人世?
“卿卿,你且先看看这个。”
李衿将手边那张状纸递与沈静姝,沈静姝狐疑地接过,低头细细读起来。
却不料,竟是一纸泣血椎心的控诉!
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即便是沈静姝这局外之人,心中也尤感愤慨。
“这怎么会!?”
世上竟有如此蠢笨愚昧又厚颜无耻的丈夫?
李衿点点头。
“我早在李桐身边安插了眼线,其中一人正是他的心腹,李桐暗中绑架这些商户勒索钱财的事情,他早向我传报过。”
“这些商户大多是受了胁迫而不得已附逆,其情可悯,但有一部分,是存了投机之心。”
士农工商,商是最末等的户籍,太宗时期,商人之子甚至不许参加科举,只能子承父业,世代为卑贱的商籍。
而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散尽千金疏通人脉买官,二是投机入仕。
正如武后的父亲武士彟,起初也只是一个木材商人,但依靠着出资为高祖招兵买马,最终拨得一个功臣头衔,一跃为士。
“所以李桐也分了两种手段对待这些商户,一类只是逼不得已附逆的,严加看管,纵容亲部军士施加虐待,而另一类党附于他的,则好酒好菜招待。”
“真是蠢人!”沈静姝道,“党附谋反之罪,罪连三族,这些人未免太过于妄想。”
可偏偏就是有人抱着侥幸投机。
“其实李桐的算盘我也能猜到,”李衿说,“商人多财,日后若真是成了事,只消随便拨几个头衔打发这些商户,以后便可以私人之名让他们继续贡上钱财,为自己挥霍。”
沈静姝点头,转而又看了看那状书。
安氏娘子的丈夫,那位陈家的郎君,便是个想要投机的蠢人,不仅拉上自家蠢儿,竟还连发妻都不放过。
但安氏何等聪慧,一眼望穿李桐的居心,原本是想虚与委蛇,谁知竟被丈夫出卖。
鞭打刀割,甚至用了妇刑……状纸之言字字泣血,沈静姝光是想想都心惊肉跳。
也幸亏是还留着一口气。
为云六娘感到庆幸,沈静姝随即又急问李衿:“那安氏娘子可还能完全治好?”
李衿摇头,“不知道,状纸是另一个女商替她写的,听说她高烧昏迷,能撑过去倒是还能有些希望。”
沈静姝默然,片刻后突然问:“衿儿,我可能去看看她?”
毕竟是受人所托,沈静姝也想尽力而为,李衿当即同意,唤了婢女进来伺候。
两人正自更衣,突然有人来报。
“殿下,门口来了个疯娘子,硬要闯进来见驾,说是有冤情相诉。”
……
云六娘蓬头垢面,跪在幽州都督府门前,磕头磕得额面都青肿渗血。
那日虽是拜托了沈静姝,但她始终牵肠挂肚,最后决定亲自赶上幽州。
可才到洛阳,便听说幽州有叛乱!
云六娘又连夜急往幽州,可等她到时,幽州叛乱已被长公主雷霆手段镇压,正自处理那些附逆的军士和其他有关人等。
她不知道阿卯有没有在其中,人生地不熟,她只能跪在都督府门前,求见长公主。
此刻烈日骄阳,灼烤着她饱经风餐露宿后干裂皮肤,无情地攫取最后残余的水分。
云六娘嘴唇干得起皮,喉咙也因为彻夜的痛苦而嘶哑,几乎发不出声。
她分明觉得滚热,身体却在打冷颤,虚汗直冒。
阿卯……
支撑云六娘的念头里只有这两个字,她要救她!
跪了不知多久,意识几乎要烧尽,却在这时终于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六娘,你快起来,你的阿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