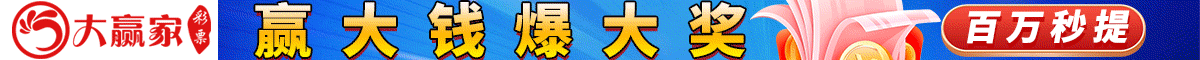《春莺啭》 - 番外二:32
他先识得她、欺负她,与她关系是势同水火,又去韦保琛那讨了药,对她下药。
大哥因他识得她,从他手中救了她,阴差阳错与她有了肌肤之亲,继而成了婚。
这中间他还与她有过纠缠?
他脑中一团乱麻理不清,抑住杂乱心绪,靠近她道:“莺莺,你与阿骧之事我既知晓,又与你成了亲,自不会再介意旁的。今日我几番追问,不是心中有刺,是有些记挂远在川蜀的阿骧,还有我方才在书房竟见到了这一条丝帕。我想着恐是你从前用的。”
他一手撑在枕间,俯身对她解释,又将那条他私藏许久的丝帕递给她看。
她怀了身子,较从前更易悲喜不定。他同她解释,她心中委屈难以排遣,不由双目含泪。
待见了那丝帕,她亦是愣了一愣。
那方丝帕是她多年前在安源所用之物,丝帕边角绣着的花鸟还是她十岁时的女红手艺。
她道:“这丝帕你是何处得来?”
他道:“我亦不知,我是在书房中无意寻得。”
她道:“这是我十岁时所绣,只在安源用过,并不曾带到京城来,怎地会在你书房?”
果然是她之物。他将从她那得来的小物件好好存着,哪里像会欺负她、与她水火不容的样子他为何又要给她下春药。
他想到几日前清晨起床,二人间的情事,似有些明白自己为何寻韦保琛要春药,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真会做出那般强迫女子之事。
大哥都将他额角砸伤了,似是佐证了他真的犯了浑。
他继续道:“我已是记不起为何会在我书房。我想着会不会是阿骧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你我已是夫妻,阿骧也忘了前事,你莫要再背负那些不肯放下。”
她亦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想是自己多思了。从前他几回求亲,是她拒了。他从未有介怀她过往之意。
她想了想,许是他双目复明后,与从前的他很是不同。二人间的亲密无间她最是能体会。他与她始终隔着一层,有时候竟也小心翼翼。就像这方丝帕,并非甚么要紧事,他似是藏在心中猜想许久。
她心中隐有不安,故而她有些草木皆兵。
她道:“是我孕中多虑。这丝帕许是如你所说,是阿骧带来京城的,它是我安源日常所用之物,想来也只有阿骧能接触到。我当年自安源来京城,带上的绣帕是母亲特意用了旁的料子重制的。”
他只想知道这丝帕主人是谁,既已知晓,便不想在旁的事上多做纠缠,尤其方才还惹了她哭。
他道:“莺莺,你与阿骧之事,我既一开始不曾介怀,往后都不会介怀。你亦说他忘了前事,日后自有他的缘分在。我做他大哥,怎会想不通这些。”
如莺以手轻抚小腹,那处已微微隆起,道:我怀了他们,你又忘了前事,我是有些患得患失起来了。
他知晓自己不比大哥,与她一处,心里虽欢愉眷恋,但却是冒名顶替得来。心始终是虚着,不敢彻底敞开了同她相处。
他道:“对不住,都怪我好些事想不起来。你往后多说些我们从前的事给我听,说不定我便能想起来。你若肯,也说些阿骧、祖母他们的事,旁的姐妹也可以。”
她点头应下。
他陪着她在花园子里散步消食,她的身子一日日重起来。
园中盛放的金菊换做腊梅,秋日变为冬日,他已将她和大哥、还有自己的往事听得清楚。
虽然她谈得多是大哥与她之事,但他还是能梳理出许多自己的事来。
如莺临产恰如那巫医所言,是在腊月中。